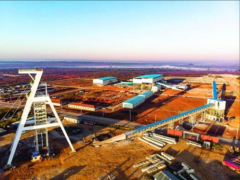当然,这并不是什么互联网时代的新鲜事,在电报发明之初,评论家纷纷畅想说,这东西能让“各国的外交家们坐在一张电子谈判桌的四周,世界和平也便指日可待”。谁曾想,几十年后,世界大战中,电报成为了战时通讯的重要手段。
按照Tom Standage的说法,历史总在“转推”自己。从电报到社交媒体,在新技术初生之时,我们经常会采取一种聚焦收益、淡化威胁、忽略成本的思考策略。这种策略热衷于询问新技术带给我们什么,却很少关注新技术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。或许,在热情的欢呼中,后者太不合时宜。
不过,对于学术研究者而言,这种聚焦成本和威胁的“逆向思考”,却往往能帮我们生产更多的启发性概念,再用这些概念反哺进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。
逆向思考一:从彼此相连到无限缰绳
Facebook在自己的企业宗旨中说,它想帮助人们彼此连接,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亲密。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,社交媒体单凭一己之力,就实现了“天涯若比邻”的古代梦想。不过……等等,若老板是我的天涯,那么就让TA岁月静好地呆在天涯,好不好?Facebook说,不好,我想让你们变得更亲密。
在研究劳工问题时,邱林川教授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说法:无限缰绳(wireless leash)。这一概念发端于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察——流水线工厂的老板在员工入职时,会发给每人一部小灵通,这样一来,老板就可以随时随地都能找到自己的员工。
事实上,“无限缰绳”隐喻的宿命又何止于流水线上的装配工。使用社交媒体的我们,在随时随地、免费快捷地找到所有联系人的同时,也都可以随时随地、免费快捷地被所有人找到。
我们圈住一群人,又被另一群人圈住。当然,圈住我们的人也不必得意,因为自有人来“圈”他们。我们通过微信,将这个世界变成一个“圆环套圆环”的游乐城。永远在线,彼此搏杀,全都是俘虏。一起出逃如何?Sherry Turkle感慨说,十几年前,“独处”尚且是种美德,如今若是你关掉手机、电脑、iPad,效仿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,独自去往阳澄湖,陪鱼蟹过几天闲散日子,那一定是种诡异的避世感。且不说什么山河湖海。一位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段子:有一天他去咖啡馆工作,突然无意中看到,窗边坐着一个喝咖啡的男人,这个人没带手机,没带电脑,也没带iPad,更没有和别人聊创业聊投资,他只是在认真地喝着他的咖啡。有时候呢,还放下杯子,看着窗外微笑。他观察了很久,最终得出一个结论:这哥们有病。
逆向思考二:从User生产内容到Loser生产内容
如果Tim O'Reilly看到“在场”这种说法,恐怕会摇摇头,这远远不够,我们要“参与”。
还记得那年火遍大江南北的《维基经济学》吗?它高举维基百科的成功,劝告我们,“人人献出一点爱,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”。等等,似乎不太对,因为维基百科好像是“非盈利“的,怎么扯上了经济学?
除此之外,大量的实证研究还告诉我们,网络论坛的绝大多数用户,都是不怎么发言的潜水者(lurker),这又如何解释呢?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跳了出来,重新梳理了一下其中的逻辑。你看啊,情况是不是这样的:少部分用户贡献爱,大部分用户接受爱。最后,资本用爱换了钱?丹麦学者Søren Petersen吐槽说,这哪是什么参与,分明是赤裸裸的剥削。User-generated content? No, Loser-generated content.不如我们再次试试看,拒绝参与这场Web 2.0的游戏。我在研究访谈中遇见过不少被社交媒体所累的年轻人。我问他们,如果无法拒绝使用微信,那么如果试着关掉自己的朋友圈呢,会不会好点呢?他们听到这个问题时,凝视我的眼神,就像在凝视一个外宾。Daniel Trottier在访谈中遇到了大致相同的情况,受访者坦白说,他们加入Facebook并在上面维系一种“积极”的状态,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社交压力,因为这是一种社交回馈行为(reciprocal activity)。

别人都在朋友圈中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心路历程,就你搞特殊?关键是,你不发,还看我们,凭什么?这就好比,对方浑身上下就穿着一条游泳短裤,你还西服革履地给他点了个赞。
逆向思考三:从参与式文化到参与式监视
最后我们再来思考一下监视问题。“在场”“参与”和“监视”,三者某种程度上完成了社交媒体使用的闭环。他们并非彼此独立,打个比方,互联网上有种说法叫“吃瓜”。想想看,吃瓜的前提,是有人种瓜。没人种,只能吃土。我们的在场和参与,都是在种瓜。吃瓜的我们也不必得意。因为我等芸芸众生,也逃不出瓜的命运,同样也是要被吃的。学者Jose Van Dijk吐槽说,那些致力于保护患者隐私的医生们惊讶地发现,患者自己已经在脸书上把所有的事情抖了出去。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,我们被吃的瓜,都是自己主动种上去的。当Henry Jenkins在倡导互联网时代的礼物经济(gift economy)和参与式文化(participatory culture)时,研究者为这种“种瓜给人吃”的行为,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:“参与式监视”(participatory surveilance)。也就是说,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主动“交代”自己的信息,实际上,这些数字痕迹,都可能成为监视者收集的潜在素材。
另一方面,“参与式监视”也可能是帮助监视者提供他人信息,成为监视的“帮凶”。
2018年11月,一位某国内大学的老师收到了微博私信,发信人倾诉了自己在大学校园中遇到心爱的女孩,却失之交臂的遗憾。这位老师便在微博替发信人寻找这位姑娘,也确实得到了20多位热心者发送来的女生的照片和个人信息。随后发现,发信人是一位游荡在这所大学多年的跟踪狂。貌似善意的“人肉搜索”,却带来了个人信息的严重泄露。